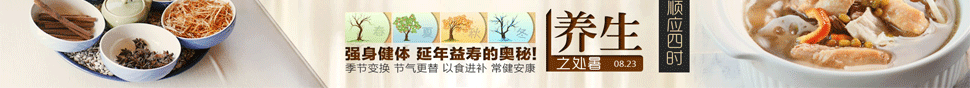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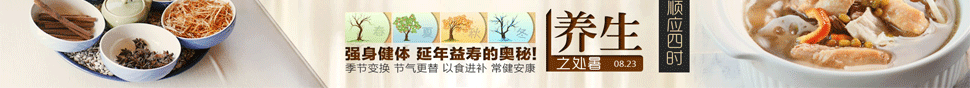
青盟圆桌|
居住反思:养老与居家生活
导语
在与百万庄居民接触之前,我们从来不知道一个小区里,老年人可以占到居民的大多数。
疫情凸显了他们的脆弱,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老年人需要什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当下的养老设施配套是否足够?以及,在真正的生活中,这些设施的使用有没有什么不足?
疫情带来的另一面,是“家”空前的重要性。我们可能从未与家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这么久,家也忽然变成了生活的全部。几个月的居家生活结束之后,我们对住宅空间又有什么新的审视?
在这样的思考之下,青盟在对小区“封闭还是开放”的讨论之后,继续探讨养老与居家生活。
圆桌嘉宾
(按正文发言次序排序)
魏维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起草人员之一匿名管理者
不愿透露姓名的社区管理人员
王羽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适老建筑研究室主任顾宗培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起草人员之一于小菲
海淀区四季青镇责任规划师,一级注册建筑师,注册城市规划师王宏杰
“爱上百万庄”志愿者-城市规划师蒋朝晖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起草人员之一
养老
封闭管理期间,小区是如何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如何获得一些日常必须的生活服务?
疫情期间生活不便的老人确实有困扰。我们知道有老人2-3个月都没出过小区,因为发现他们都不知道有出入证这件事——可见他们从春节开始就没出去过。很多老人家里是有保姆的,但这也要分两种情况,长期住家的保姆可以继续在老人家里,但有一些每天去老人家的保姆、或小时工,就存在进不去小区的问题。最近这段时间,可以进小区了,从审核上也会比较严格。所以那些“低龄”老人,反而会存在比较难兼顾到的情况。
就餐方面,有的小区有老人食堂。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要求,可以订餐,从卫生和价格基本上有保障。订餐如果老人能自己取,我们会把食物放门口,但如果自己没法取,就还是不行。
目前的这种情况下,老人的日常需求主要是哪些,按照急迫程度来排序的话。
对有子女的那些老人来说,情况比较简单一点,主要就是购物和看病。但如果是纯高龄的家庭,情况就更复杂了,照料、看病、日常陪伴的需求,都比较高。
如您所讲,老年人就医和买药是重要的需求之一,疫情期间老人的就医和药物采买,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我们这里,就医和买药还比较方便,小区附近有一个卫生服务站。日常开药都可以通过这个,卫生服务站是可以上门的。
现在这种情况,老人的很多需求是没有释放出来的。比如我家里的老人70多岁了,之前为了减少感染风险是基本不出门的。直到弹尽粮绝了,才去小区里的小超市采买。后来小区觉得超市要进货对外接触频繁,有风险,就给关掉了,年纪大的人生活就出现了很多困难。老年人无论从心理层面还是身体情况抗击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是比较很差的,他们会尽可能压缩需求,简化生活。然而,老年人身心特点决定了他们无法长时间不接受外界的帮助独立生活,就餐、就医、交流(以消除孤寂与不确定因素带来的恐惧等)都是日常需求,不能断。疫情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很多问题,以前有一些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帮助,但疫情发生都无法正常提供服务了,小区周边的商业也停止营业,影响最大的就行行动能力有限的老年人群,我们正在研究怎样利用技术手段去弥补目前显现出来的一些短板或问题。
其实看病和就餐还是基本需求,有一个大家很难注意到的是陪伴的需求。老人倾诉的欲望是很高的。心理学的专家和我们建议,陪伴应该由陌生人来,说是更容易让老人说心里话,但实际工作里,如果是面对外来的党员志愿者,老人也就尴尬地和他们聊20-30分钟,放不开。老人需要的精神慰藉,还是来自于认识的人。如果是他们信任的社区工作人员去家里,他们自己一个人,就能说两个小时。
从老人的服务上来看,目前的症结是什么呢?
在服务方面,我们真正的希望,是有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从社区这块来说,我们能做的,是帮助居民去联系专业的服务者。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专业的人”?北京市政府对老人、对失能老人有一个补贴,但要找到真正足够“专业”,可以服务老人的人,是比较难的。比如“助浴”,一次元,价格不低了,但来的人却不一定是专业的,可能只是个普通家政人员。再比如适老设施的改造,这个设施可能是专业的,但来安装的人未必专业,可能就是施工队,他在安装的时候,体会不到老年人的需求,最后结果就是大家花了钱,买了好东西,但就是不好用。
还有“喘息服务”,这个是为那些完全卧床老人的家庭提供的,因为他们的家人如果是全天全年无死角陪伴,压力会非常大,需要每周有一段时间找人来替代自己,休息一下,用这个“喘息服务”。这个工作从费用上比较高,但能做这件事的机构也非常少。我们去找的时候,一个是可能根本没听说过喘息服务,第二个可能就不理解我们的需求,就派一个家政人员来,没有我们需要的资质。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能照顾失能老人,同时具有护理、家政的能力,也不一定会来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对引进这些队伍是很慎重的。很多人说你们社区老设置门槛,但是政府和社区都是要有公信力的,我们得保护老年人。通过我们引进的团队和服务,老年人更容易接受,但这个风险我们就只能替他们担着。
一边是需求特别大,另一方面专业团队没有合适的入口,非专业团队把市场做乱了。很多人都想进入这个市场,做好事,但之前的人已经把事情做砸了,现在新的这些人就得面对很多门槛。
如何理解后疫情时代的(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或(北京采用90%居家养老,6%社区养老,4%机构养老),我们是否要反思当前的养老模式?
更多老人还是更愿意居家养老。如果居家养老外围服务能够跟上的话,是最好的选择。对疫情这类突发变化来说,老人反而比年轻人更自律。他们虽然有盲从的情况,但很多时候对信息是有分辨能力的,让我们很省心。这次疫情给我们很多支持的,恰恰是社区中的老人。我们很多的志愿者也是老人。年轻人想法更多,顾虑更多,但社会责任感比老人要差。
十三五期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国发〔〕13号),强调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的发展目标。不管是,还是,都强调大多数人在家里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度过老年生活。社区发挥一些作用,当需要非常专业的照护的时候,才是必须到机构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日本也是在经济发展特别好的时候,建了很多养老院,但是近些年也在尝试社区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让老年人能更长时间地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我感觉不管是疫情是否发生,这个大的趋势不会发生变化。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方式。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我们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怎样一方面是要让老年人的生活是安全、顺畅和便利的。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服务人员能够有合理的劳动强度、待遇和收入,两者达成合理平衡的状态,一方工作压力过大,状态不好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到另一方。日本的养老服务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通过采访一些一线工作的专家,也了解到,目前日本提供养老服务的工作人员也面临社区上门服务强度大、持续工作时间长等压力。我们国家的城市尺度远大于日本,仅从这一点来看,在服务上就需要投入更多,耗费更多时间和精力。需要结合由下而上的摸索去清晰服务模式,制定扶持政策,从城市到社区到住宅,硬件建设上给予充分考虑。规划设计层面也要根据老年人口规模、服务需求确定合理的设施密度、服务范围。
在目前的居住模式下,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来辅助社区服务工作是我们重点研究的内容,不能光靠家人,这是不现实。怎么从规划设计、智能化辅助手段等不同的层面提升服务覆盖面和效率。这些也是疫情引发的一些问题,经过疫情,我们的确看到了很多平时隐藏的问题。就如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家周围的菜场、超市很方便,但一旦疫情发生了,小区封闭,店铺关闭,怎么办,这是规划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住宅
通过改善建筑设计,是否有可能提升住宅的“抗疫属性”?
住宅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没有必要因为疫情对住宅赋予太多符号和概念,我们的住宅概念已经很多了。对建筑师来说,套型的设计只要按照相关(《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住宅设计规范》、《住宅建筑规范》)规范的要求做,就完全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居住需求了。规范对于日照、采光、通风、设备等涉及健康卫生方面的要求已经很全面,设计的时候不要钻空子、不要打擦边球,老老实实地做就没有问题。住宅其实不需要太多花哨的东西,最首要的一点是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增加更为精细化的设计。比如说,卫浴设施分离设置、门厅增加洗手功能等等,这些设计其实不是针对疫情的,而是随着人们对于居住舒适度、整洁度的要求不断提升而出现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整体住宅市场对于精细化设计的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sijiqinga.com/sjqtx/629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