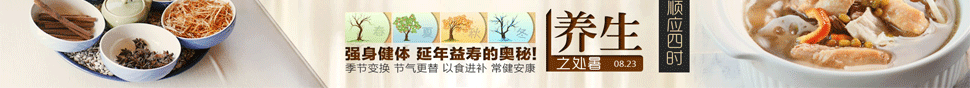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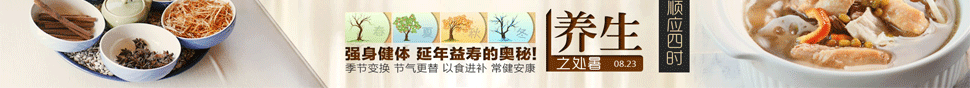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周万芬,原电白盐场办公室主任,曾有较多新闻、通讯稿刊于茂名日报、羊城晚报,近期有作品发于电白报、高凉文学,是一位50后的文字爱好者。
??????????今日看白蕉
?白蕉,在古镇电城的西南,与千年古港博贺隔海相望。
?白蕉,有山有海有盐田;有船有港有码头。
?白蕉是个好地方!白蕉有过白礁的过去,四周是海,白茫茫的大海一片,海边礁石峋嶙,所以有过白礁之说;后来青山绿了,村庄靓了,连同田野的道路都鲜花竞艳,蕉树成林,且盐田银滩,白雪皚皚,因而定称为白蕉。
?多年前,我的先祖在白蕉西北面一个叫“牛乸潭港”的地方钓鱼,就看上了这块多情的土地,爱上了这个富饶肥沃的地方。当时他说“在这里就是拾沙螺也可以养家糊口,富甲一方”。他看重这里的小山一年四季青绿滴翠;他钟情这里的海滩潮起潮落,有一片广懋而肥沃的滩涂;他认准这里一片片盐田将来会是一个“大器皿”;他说港口码头船舶可通达四面八方。于是,他立此为家,繁衍生息,发展为村。60多年前,我也是生于此而长于此。在此20多年的生活,劳作,观察,我对此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垄,一寨一屋,甚至是一人一事,都是那么的眷恋,那么的情深,这里的一沙一石,一砖一瓦,一座祠堂,一间草屋,都是那么的情真意切,铭刻心中,挥之不去,历久弥新。我的根在此,十指连心,不管漂游何处,身在何方,白蕉,都是我不可抛弃的家乡!
?有道是“落叶归根”,候鸟归巢。今天,40多年在外漂泊,一枚游子的我,再次回到白蕉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一路走来,那山山水水,沟沟壑壑,每一条乡道,每一个村寨,既是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的陌生。熟悉的是名字,陌生的是变化。村还是那个村,名也是那个名,只是面貌已今非昔比,变化无不让人惊讶,让我感慨!
?
?????????田垌已没了田
?如果要把人比作是一株植物,那么白蕉田垌就是我初始发芽的地方。
?白蕉村中有小村,而每条小村都富有个牲特点,都是以它最为突出的地理特征来起名。田垌,顾名思义是在田野之中。我记得,从我懂事时起,田垌这小村子,房屋最好也只是泥砖墙盖的瓦顶,一家一户也得一二间,房子最多的算是我家了,村巷通道西三间,东两间,五间土坯屋,算是出了名。当时村里最有特色的,那就是“勤奋起家”的“地主屋”了,三间两进两拖廊,十多间房子挤成个“国”字,但也全都是泥坯砌的墙。
?小时的我,十分的喜欢走村穿巷,走过“胡二奶”的居家,是两间泥坯盖的禾草,我也不知多少次由母亲带来此处避台风,风中摇晃,风雨飘摇,惊心动魄,想着都不寒而栗。来到“国二奶”的住宅,同样是三间草屋,只不过门口有大大小小一排的兰麻树,炎热的夏天,全村男女老少都会在此乘凉。“国二奶”草屋门前,就是村子里面当时的“讲古场”。村民在这里,既说一年四季的种养经,也说梦想,说变化,说些憧憬的美好未来!
?那时的我,走出村边,一脚踏下,就是肥得流油的水田了。我记得,“地主大屋”的东边,一片的水田叫“后门仔”,这里有过我的耻辱,也有过我的辛酸。后门仔田的番薯硕大无比,但我可望而不可及;这里还有过一丘蕹菜田,我曾手挂一只篮子,来过这里,踩下没膝深的烂泥,摘过夹着紫色菜花,带着绿色菜籽(如古纽扣状)的蕹菜回家当饭充饥;西边,与村子仅隔一片竹林的地方,也是一片田垄,这里叫“西面田”,水稻生得比我还高出一截,这里的早田薯十分苗条均匀,红红的,嫩嫩的,让人垂涎欲滴;村子后面,小山脚下,一大片的水田兼坡地,是种水稻和花生的好地方;来到“国二奶”的兰麻树下,一大片的水田,一丘接着一丘,一望无际,这里叫的门前田。门前田有过很好的故事,田与田之间,有自动排灌渠,渠外有沟,叫排洪(水)沟。沟渠保证了水田的旱涝保收。门前田的田埂,一格格,把块块田垄划分成方形,田埂可做农机(拖拉机)的机耕路,路边种上了菊花和夹竹桃,间尔种上香蕉。一株花一棵果,这么现代化的田野,本应天上有,但它却偏偏出现在白蕉。门前田的“番薯楼”更是远近闻名,曾引来参观者无数。一年年,一辈辈,田里从青绿到金黄,从金黄到青绿,春夏秋冬,为村人提供就业,提供食粮。我也觉得,我们村子,就好像田字里面的四个小方格,而农田就是田字外的四条边。“田垌”一名,形象,中肯,生动,实至名归。
?田垌是我今日看白蕉的第一站。老骥索途,我沿着小时走村穿巷的路径,寻找胡二奶茅屋的地址。旧时狭小而弯曲的老村巷,己被更新拉直,巷口阡陌的泥砖瓦房,再也看不见,泥墙变红砖,房顶变了样,身肥了,体壮了,还长得高高了。好不容易来到胡二奶原来的住址,草屋已不复存在,原地高楼建了起来。看看“国二奶”的草屋吧,我穿过一座座别墅型的建筑,来到古时兰麻树所在地,“国二奶”的草屋早已变了样,连兰麻树也隐身退出,给了新建的楼房让位。
?到了摘秋后蕹菜的后门仔,村民告诉我“田垌早已没有田”。一座座新房,如一枚枚春笋,屹立在这片土地上。西面田,不仅起了屋,而且有了小村的停车场。我蹒蹒跚跚来到门前田,“哦,这里建起一条街”。我笑笑问乡亲“田是立基固本的基础,没田了,吃饭怎么办”,乡亲说“田都征收搞开发,村民洗脚上田了,谁还吃秋后蕹菜捞稀饭!”这话说得正是我过去的痛点,但掷地有声!不错“谁还吃秋后蕹菜捞稀饭!”这是村里的新起点,一时,我听到村子里缭绕着久久的回音。
?
?????????井头老井依旧
?
?井头,是因一口井而得名。
?井头离田垌不远,除一口小鱼塘外,隔的就只是“后门仔”的田。我从老家往井头走,已分不清哪是井头,那是田垌,两条小村已牵手在一起,难舍难分。
?来到旧时的老井,水漫到井口。井口四条麻石条依旧不动,只是井边石头围栏上长出了厚厚的青苔,漫边的井水显得浑浊。我问井头,为何能有此模样?井头问我“那时挑水的人情况如何?”
?井与人都一样,相处时间长了,就产生情谊。老井与白蕉共生长,吃水不忘挖井人。我关心着当年井台如戏台的老井,为什么会陷如此冷落,老井却关心着原来排队挑水的村民,是否都过上了吃自来水的市民生活。
?老井是一位百岁老人,它把白蕉的立村、发展、变化等千百年来的历史装进了井水,装进了井口的空间。……
?看到满面沧桑的老井,我就想起小时候,三更半夜,母亲挑一担水桶,挂一只夤壳,背上我,吟唱着“月归归(光光),小蛹子(小孩子)洛蒂陀(玩耍)洛过村……”的儿歌,讲述着“拾到女儿莫嫁白蕉村,一夜舀水到天归(光)……”的故事,头顶满天星斗,脚下一路坎坷,与我来到古井边。
?井头周围,围人一圈,舀水的夤壳,七上八下,好不容易,母亲才打上一壳水,一个小时舀不满两桶水,我已在母亲的脊背哭闹得“死去活来”,滴水贵如润,在白蕉是个最好的诠释;井头外围,还有一排长长的水桶,排得就像一条龙,时不时,还有来来回回等着舀水的人。
?从日头起到日头落,从日落又到日出,井头都是人流不断。俗话说,三个妇女一个圩,井头打水的妇女不止六个了,给它两个圩,不算贴切,给它一台戏,但它比戏台还兴浓。打水的女人,把井头当成诉说苦乐的地方,她们一边打水,一边交流,委屈也吐了真言,发泄了不满,心里便轻松舒服,喜悦也说出来,同大家共同分享。井头也爱听她们的故事,井水早已把她们的故事收藏。所以,小时候的我,经常都听到人说“井台就是戏台。”
?而今天,井头却是如此的静谧,翻开老井的故事,它告诉我,白蕉是滨海第一个通自來水的村庄,老井完成了历史使命,村中妇女,因自来水流进千家万户而也从舀水的繁琐中解放了出来。
?
???????东边园不再见酸菜缸
?
??东边园,真的园在东边。园,在白蕉是相对于水田的坡地。
?因村小学就在东边园村边的一个寺庙里,那时读小学的我,东边园是上学放学的必经之地,对东边园的内内外外,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说来也怪,因了东边园,连改作小学校的寺庙也叫做“东排宫”。
?从家里出发,穿过“公打石”,穿过“陈氏宗祠”,穿过几株“羊剝狗”(一种树,结的黄色果子可吃),也就穿过了东边园,到了“东排宫”学校。
?东边园让人有北方山村的感觉。走下村口的五株“羊剥狗”,一个长长的下坡到了学校的大门;从学校往家回,经过东边园全是上坡路,一脚比一脚陡,坡道走尽,五级用石板铺就的台阶正迎着你攀登。登上五级台阶正好是东边园的村口,直走,是一条狭长的村巷,两边黑咕隆咚地排列看低矮的民居,一间紧挨一间,让人有种越走越深幽的感觉。
?村头的“羊剝狗”树,高崇挺立,胸围粗壮,一个人围抱不了,树杆长满一塔塔的疙瘩,显示出经年的沧桑;卷卷的树叶丛中,挂满一粒一粒如黄玉米状的果儿。酸酸甜甜的黄果子,并没有树根下的酸菜缺抢人眼球。一个门口一棵树,一课树下几只缸。缸夏秋天装水,冬天季载菜,水是劳动血汗,菜是丰收果实。
?东边园的园是在村中一个叫后山岭的小山下,这里春有菜苗夏有瓜,秋有豆角冬有大芥菜,一年四季青绿。菜苗记载着村民的梦想,瓜果书写着村民的勤劳,豆角悬挂着村民的智慧,芥菜承载着村民的喜悦。
?每逢冬天,路过东边园,看到的就是一个菜品加工场。白的箩卜,绿的芥菜。萝卜用刀切开片,大的四片,小的两片,再来一层萝卜一层盐叠放在缸里;而芥菜是先在太阳光下晒一天半,去干水后,一层菜一层盐地踩入缸中。
萝卜腌制萝卜干,而芥菜则是腌菜酸。
?年年月月,东边园的酸菜缸,各家的在各家门口,各家的在各家“羊剥狗”树下。酸菜缸在向人们展示,这里的村民勤劳有智慧,这里的村民多都是菜农。
?今天,我照样是沿读村小时所走的路,寄行在高耸入云的洋楼下,显得我比读村小时更小,在一间间的民居小楼下行走,我已经是一粒蚂蚁那么渺小。一路所见,“羊剥狗”树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一株株新花,酸菜缸没了踪影,每户人家的门前都置有小花园。
?我来到昔日的村小东排宫,寻寻觅觅,只有心中曾经有过村小的存在,宫里再找不出村小的容颜。原址重建了寺庙,名字叫做“玄夭宫”。
?宫是一种信仰,村民走进宫里,祈祷前华厦伟大复兴,祈祷着幸福的日子地久天长。
????????周屋门楼全是楼
?周屋门楼,在村的入口,靠近海边,高低好歹,连几十公里外的对面海都可看到,好歹都算是白蕉的门面,窗口。
?周屋门楼,姓周,与我们田垌仅是六代宗亲,血缘关系还非常的亲近。周屋容易理解,但门楼从何而来。
?周屋门楼与东排宫仅一块小坡地之距,刚入村小时,就听村里老人说,周屋门楼很风光,锅耳屋,有门楼,门楼顶上有凤凰,白蕉有钱大户集中在周屋。入村小后,那块坡地已改造做学校球场,村小就与周屋门楼连了起来。
?根据老人的传说,在校的闲暇时,我便巡城马般巡视着周屋门楼。一家一户,我点数着,寻找着老人传说中的的门楼,寻找着锅耳屋,寻找着楼顶上的金凤凰。
?我找啊寻啊,只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堵灰沙黄土混注的残墙亘垣,在另一名看到一个危危欲坠的火砖小围墙,围墙的一端,有间如城堡样的小屋,留有细小的“猫窗”,小屋细看似是两层小楼房。另一端围墙的顶上,摆放有一株用破瓦煲栽种的丁蕊草,一株用破面盆栽种的螺花。
难道这就是门楼?也许老一辈人对门楼的认识肤浅,也许是老一辈人对门楼有着祈昐。
,一晃,我在村小的6年过去了,门楼依旧……一晃40多年过去了,这里己让人刮目相看,成了白蕉的门楼!
?看完昔日的村小,我一脚跨过周屋门楼的境地。
?映入眼帘的是,周屋门楼己全是楼,且全是高大上的现代化洋楼。要不是熟悉,咋说也会认为那是保利大都荟的“兄弟”俩,要不,这里的楼盘为你能与保利“手牵着手”,并肩向上比高低。
??????坎头龙舟码头五龙齐出海
?坎头,是白蕉龙舟码头所在地,也是白蕉运输船停泊的港口。坎头,名称不是十分文雅,但十分形象贴切,从村道下到海滩涂,要经过8级大台阶,从海滩涂上村,那就是要登8个台级的坎了。
?白蕉港的海洋运输业十分发达,早在立村以前,港口就停泊船舶,白蕉的原盐便从这里集运千年古港博贺,或直接海运至香港澳门,江门广州,甚至沿西江直达桂东湘南。
?我记得,小学的多位同学,他们的父亲都是行船跑货运的,我在课余时间,也经常会到船上玩耍。白蕉港单船吨位已超吨,电帆、电帆都是大吨位远航船。还有很多我忘记了编号的内河(海)及外线〈航〉船。
?白蕉港最热闹时节就是端午节了。这一天,港口是千帆云集,码头是万人空巷。中午时分,那是锣鼓喧天,龙舟竟发。
?家乡的龙舟,是我的最爱。那时的我,吃过有肉的早饭,拎上2只肉馅的粽子,赤膊光臀,从周氏祠堂掠过,进入坎头的村道,偶而见一二卖荔枝芒果的小贩,来到码头,紧盯着整装待发的三艘龙舟,我们的小伙伴,“咚”一声跳进海水里,与海水先来个接吻,后爬上一条小船,开心惬意地看着龙舟赛。
?三艘龙舟,三种颜色,红黄蓝,寓意福禄寿,代表精气神,也代表着船民、盐工、搬运。三艘龙舟,年年如此,不知延续了多少年,讲究的是港口兴旺,村头平安。
?从周屋门楼往坎头走,有两条路可选择,一个是沿旧路,也是大路,经村圩中间,跨过几间商店,走过周氏宗祠不远,硬是了;一条新路,可直接跨越村小右边的小山就是了。
?我还是老人走旧路,从供销社商店走。先在周氏宗祠大门口驻足观望,祠堂门口,过去是演戏的广场,广场后面是一口有20亩面积的鱼塘。而今天,广场变成私人住宅,鱼塘冒出了一幢幢别墅。走在过去的龙舟路上,两边是旧貌变新颜。
?我慢行来到龙舟码头处,港口、码头都变了旧模样。博贺湾大道从旧码头前横跨而过,似龙似练,从东向西,蹁跹而来,蜿蜒而去,一切都在变化中,连码头傍边小山的石头,也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海边,守住家乡的那么海,守住长长的乡情。
?今日不是赛龙舟,而龙舟码头的人流并不少。经打听,原是白蕉龙舟拟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港码头打造成振兴乡村的旅游景点,游客来的主要是体验龙舟文化,传承爱国主义精神。
白蕉龙舟,由村民自主组织龙舟协会管理,龙舟赛的龙舟,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龙舟,龙舟也由原来的三艘增加到了五艘,一惯以来的福绿寿“吉祥三宝”,也改成了福龙、金龙、银龙、瑞龙、祥龙。从此,白蕉龙舟成了金银祥瑞福,五福临门,五子登科,五龙出海。白蕉龙舟赛出了新气象,赛出了村民幸福满满的笑脸,赛出了承前启后的爱国主义精神!
??????西墩走出了盐水的包围
?西墩属于村里一个小岛型小村,四周被盐田咸水包围。西墩在白蕉最西边,大桥河出口处,既靠西,又是墩。这不仅是它的名字的由来,更是它过去的环境是恶劣的真实写照。西墩不仅取口淡水吃不容易,就连行一脚干泥都难,村里村外,屋里屋外,都是湿漉漉的一片。有力顺口溜,描写得更是生动形象“西端西端,行路莫穿,出门湿漉,开水难吞。”
?熟悉西墩,是到那里看电影。
西墩村东南方向,有一间红砖灰瓦的大屋,大屋门口是一个宽敞的广场。大屋的主人周凤仪是“地主”,大屋被盐场购买了当工段办公室。
?西墩盐田最多,盐工当然的不少,盐场隔三差五会到那红砖大屋门口放电影。那时,全民都患有“文优饥渴症”,小小年纪的我,当然地逃不脱患上了。每当听到西墩放电影,吃上晚饭了就邀请伙伴,托上一条长櫈,早早地占据个头位。
我们心惊胆颤地踏着去西墩的独木桥,桥故“吱嘎吱嘎”,我们的心便忐忑忐忑,生怕掉下桥底,但“文化饥渴症”让我们把渴望转化为力量,为了电影,我们壮着胆子过小椅。当然,也有小孩来回都是趴着爬过去的。
??走下独木桥,沿着咸湿的盐田基小心行走,生怕一脚蹬错,就跌下盐池或陷入盐缸窟,不是湿身也是湿鞋。我们看场电影都是那么的小心翼翼,何况西墩人当时的出行,是何等的艰难。……西墩不是在水一方,西墩而且在水中央,这就是西墩留给我们的印象。
?时至今日,当我脱下皮鞋,计划离家巡走西墩的时候,家里人却说“你认为还是40年前咩,老脑筋。现在去西墩可水泥大道四通八达了,哪里还需过那提心吊胆的独木桥?”
?哦。行出我田垌村道,一条2车道的水泥硬底路笔直而去,一直向西。村民居家变靓变好,那是湿水棉花?,实在没法再弹。我只得来到旧时电影广场。
?户场上红墙灰瓦大瓦还在,只是广场改造了城为蓝球场,西墩文化广场拔地而起,电影慢慢淡出人们视线,而传统的戏剧图书却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一个文化广场,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村民学文化、长知识的平台,办好一个文化室,可为村民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盐灶,历史再改写
?盐灶也是白蕉最典型的地理标致性村名。盐灶是白蕉最早生产盐的地方,是白蕉盐的始祖。村名叫盐灶,村人也晒盐,它与西墩都一样,四围皆盐田。
?据史料记载,食盐的生产历史是,先漏沙,后灶煮,再到光晒。
?盐田是我小时候经常出入的村庄,这里既有父亲的老同事,也有我的新朋友。
?那时探望父亲的同事,一般会被带去一个叫做“官厂园”的地方玩。官厂便是最先的煮盐地,那里留有古灶的遗址。
?我用眼看,用手挖,一心想在官厂园找回白蕉盐的历史,扒开一堆瓦砾,挖出一堆石头,官厂盐的史迹已被尘封,再找也找不回。
?盐灶是白蕉水墙篱屋集中地,印象最深就是上盐灶到下盐灶村道中间,那是一排的竹子架上糊着草泥墙的草屋。盐灶是白蕉水墙篱的故乡。……
?从西墩到盐灶,路程很近,旧时是2条盐田基,现在也不过1公里。心情好,路途就短,行走也快,走在水泥硬底化公路,眨下眼,从西墩就到了盐灶。
?俗话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盐灶,我以为是在错路了,盐灶,看不到盐,看不到灶,连村都找不到了。
?原来是,凭改革开放的春风,盐灶村人发奋图强,经商的经商,读书的读书,出外的出外,入城的入城,全村移民外迁,盐灶终于改写了历史。
??十里盐田,正如先祖所说“这里的盐田将来会是国家大器皿”,盐灶,腾笼换鸟;盐灶,盐碱地上长出“摇钱树”。
????????鸡笼山变成了兴平山
?鸡笼山本来是座岛。鸡笼山有很多传说与故事,其中因其小山似鸡笼,所以叫鸡笼山。还有鸡笼山与放鸡岛也有着很多的传说和故事。说的是远古以前,鸡笼山里的鸡让盗贼打开笼门准备盗走,那鸡展开双翼飞到海中,浮现小岛,后谓之放鸡岛。
?鸡笼山因与博贺相望,鸡笼山人多以撑度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辛苦,世世代代,鸡笼山人盼望着幸福,盼望着小岛能与陆地相连……
解放后,政府为实现鸡笼山人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先将鸡笼山改名称兴平山,而带领兴平山人战天斗地,逐步过上了天下兴平的幸福生活。兴平山与博贺通大桥,同盐灶通公路,往日的孤岛变成金凤凰。
?有人说,如果把博贺港称为黄浦江,那博贺则是外滩,而兴平山就是浦东。历史的发展也确实如此,今日走进兴平山,无不看到“万丈高楼”拔地而起,市民喜笑颜开。古港屏障,古渡公园正在形成。……
?今日看白蕉,白蕉再不是一穷二白:的白;今日看白蕉,白蕉正像一只展翼鹏飞的白鹭;今日看白蕉,白蕉已是南海滨上的一颗明珠;今日看白蕉,白蕉已是博贺湾上的一座新城!
?白鹭含珠,新城展翅,向高腾飞,向天翱翔。
??(周万芬于广州湖景华厦12楼)
????????????????????????????????????????
?????????
????????????????????
????????????????????????????
??????《承泉文学》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sijiqinga.com/sjqpz/9391.html

